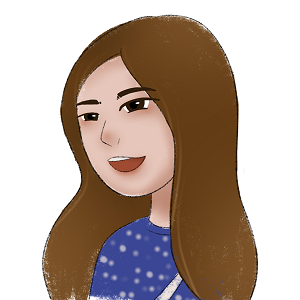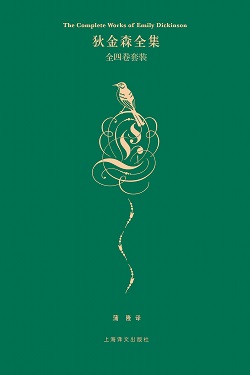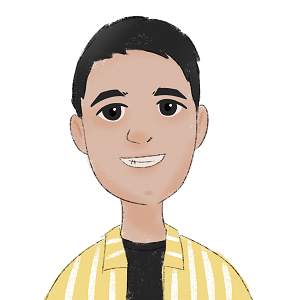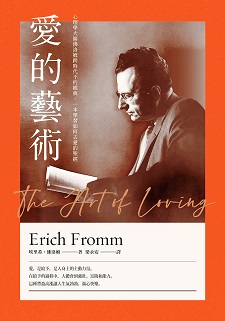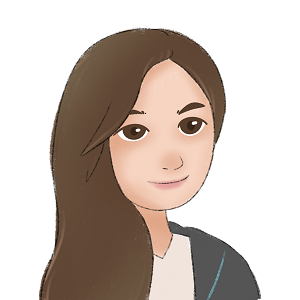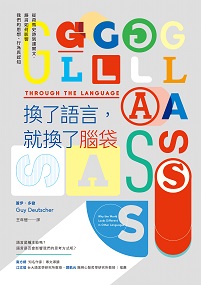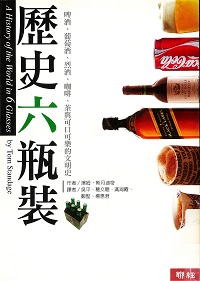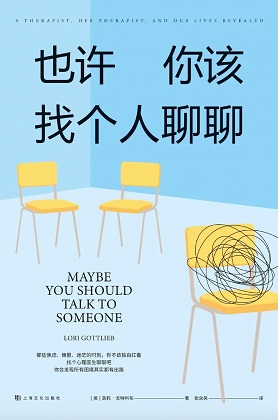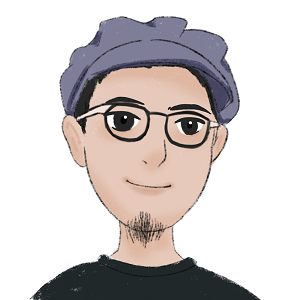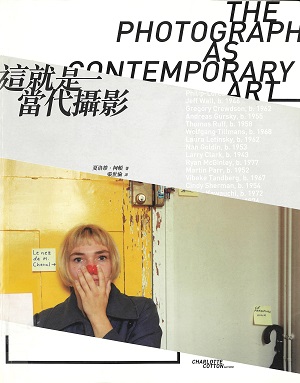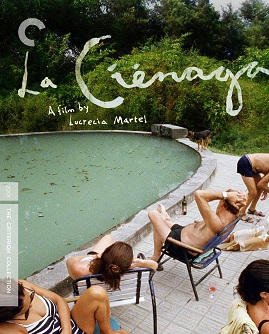2019年,笔者曾往美国纽约州伊利县,不为别的,只盼去看看曾在阿默斯特镇上默默无闻的独身女子 —— 一个生前在家里做饭、做针线、伺候老人,一生只与十来个人通信,死后却声名远播的奇女子:艾米莉•狄金森。因为这样一个人,在整个疫情时期疗癒了我。
艾米莉•狄金森出生于家境殷实的乡绅之家。父亲是镇上名人,曾一度当过国会议员,却因为保守的思想而不让女孩子在学识方面有所作为,特别是禁止她写诗,这在19世纪,似乎并无特别。哪怕是在今天,女子的教育或许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期待中的样子,每个人对于男女平等的理解也仍有距离。
于是,中途辍学后的艾米莉,出席镇上的聚会,在家中接待朋友,跟青年男子乘马车出去兜风、互赠礼物,并偷偷写诗。传言因为她计划与一男子私奔,被父发现后阻止,从此下定决心终身不嫁,闭门隐居。关于她的感情世界,艾米莉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但我想,或许这不过是世人想要了解她的诸多方式中最学术的一种。如若这般,除却今日介绍之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狄金森全集》,她的信件当真要读!并非仅仅因其内容文辞优美,遣词造句如诗如歌,更是因为不管诗歌还是信件,都是她表达自我,传递思考的方式,也是我们得以认知完整艾米莉那为数不多的依据。
然则,普遍认为她的大量爱情诗篇皆源自她丰富的情感经歷,但说着“许多人都将生命託付给神,我却将我的生命託付给诗”的她,似乎很难让人想像会真正爱上任何一个世俗男子。看她的诗歌,让人觉得她所爱的归根到柢只是其独立的自我和自己想像中的理想伴侣。这样的初衷,在我们这个强调“自我”,又害怕过度解读“自我”的世代,独立探求真理似乎比200年前来得更为不易。
但好在有诗。因为有了诗,艾米莉•狄金森说“除了快乐,我还有话可说吗?”因为有了诗,她的幽居生活看似无波无澜,但内心烈焰翻滚不休。因为有了她的诗,让拜读其作之人深感“啊,甘心孤独的人总是充满神秘感”且“读艾米莉,便是感知希望”。
若你问我该如何读诗,想必年轻人读古文总喜现译“关关和鸣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小洲。贤良美好的女子,是君子好的配偶。”但若朗读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想,情感不言而喻。今天读艾米莉,开始读就可以了。每一天,从现代人零碎的时间里,拿出喝一杯咖啡的时间足以。若实在繁忙,先跳过译者序言,读一读每个人专属的第一印象,又或者,忘却这篇推荐序也并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