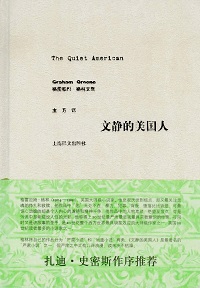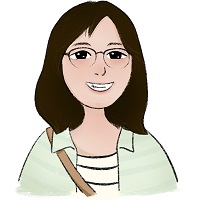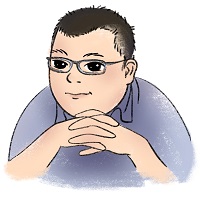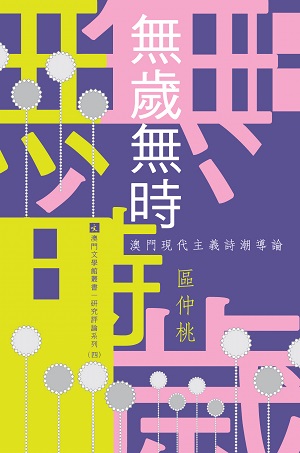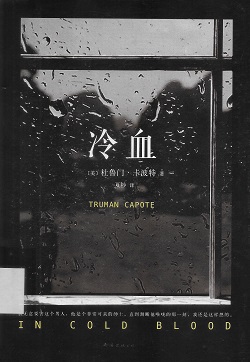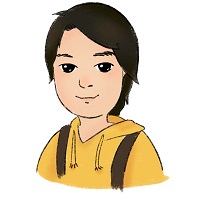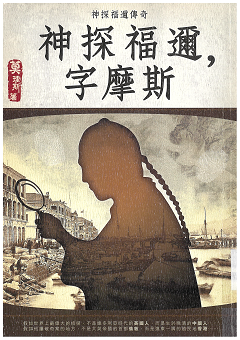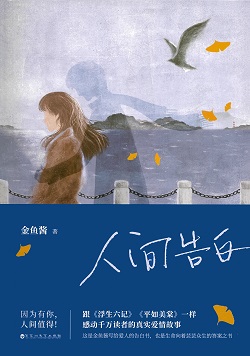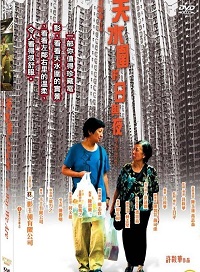關於越戰的小說不少,英國人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文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絕對是箇中經典。這本小說寫於20世紀50年代,表面描寫的是越南與法國之間正在進行的反殖民戰爭,亦即“第一次越南戰爭”;同時又極具預言性地,鋪陳越南與美國將要展開的“第二次越南戰爭”。相比起描寫戰爭慘況的煽情反戰小說,格林選擇了較抽離的角度,以偵探小說的外衣,包裝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
《文靜的美國人》寫得巧妙,巧妙在於它對越戰當下的全球主要勢力——以東方大國為首的共產主義和以現代化西方列強為首的民主自由主義,甚至還有漸漸從歷史舞台退場的歐洲殖民主義,三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剖析辯證。透過美國使館人員派爾、英國記者弗勒和越南女人鳳之間的三角關係,如手術刀一般,一層層剝開自由主義的華美表層下,赤裸裸的真貌。
在格林筆下,三人的性格和形象鮮明:弗勒極愛嘲諷,有時是為了掩飾內心的自卑。為了成為稱職的記者,弗勒遇事總保持冷漠不動情,卻始終無法拭去內在的善良和同理心;派爾像個紳士,沉靜有禮,卻迷戀於自由主義,一直相信可扶持第三勢力,解放越南;而鳳,夾在兩個男人之間,由於語言不通,個性含蓄忍讓,在故事中沒太多自我表達的空間,只能讓兩個男人去爭奪、詮釋她。她是一個腳踏實地生活,但又不失浪漫想像的女人。不懂得、不迷戀任何意識形態,卻渴求簡單的“自由”,如造訪大峽谷、摩天大樓、自由神像等異國地標。讀者不難發現,弗勒、派爾和鳳,基本上代表了殖民主義、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價值觀。而作為當時在越南嶄露頭角的美國自由主義,格林透過派爾這個人物,暗示了它的危險性,正如他會不顧一切地穿越戰場,只為了告訴弗勒:他愛上了鳳,並且要與弗勒公平競爭。這是一種令人發笑、荒謬的理想主義,為了實現所謂的“公平”,竟賭上性命。這不正正是日後被冠以“解放”之美名、賭上無數無辜美國青年軍人性命的“第二次越南戰爭”之縮影嗎?
當派爾策劃恐怖襲擊,在廣場錯殺平民後,弗勒向派爾怒吼:“在你開拓民主的疆土時,要殺死多少殖民國的軍人,才能使一個無辜的小孩或一個三輪車伕之死,死得有價值?”派爾的行為向我們展示,迷人而理想化的“概念”,有時像酒精,令人深陷其中,使一切殘忍顯得合理,使一切無辜的人都死有餘辜。放諸今日同樣硝煙四起、劍拔弩張的世界,《文靜的美國人》對於意識形態的深刻見解,仍有不容忽視的警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