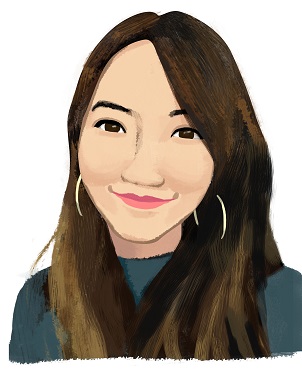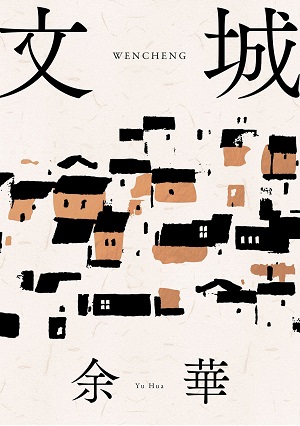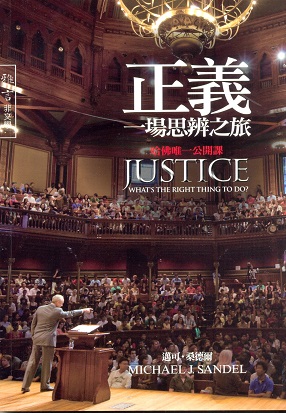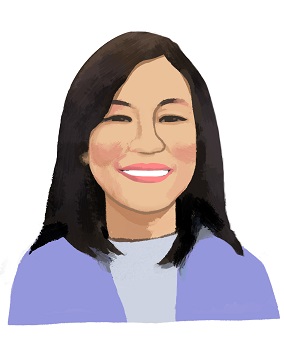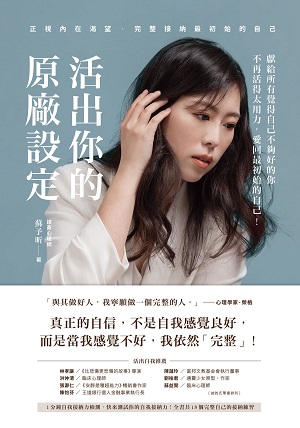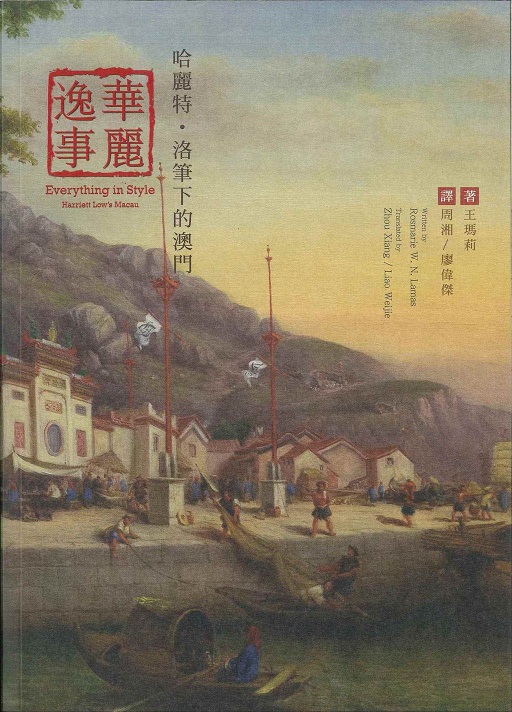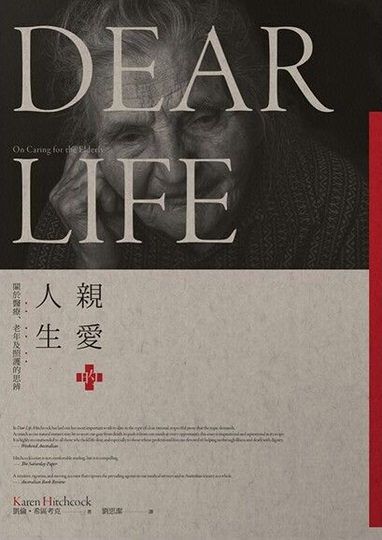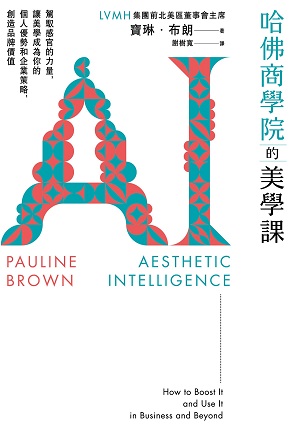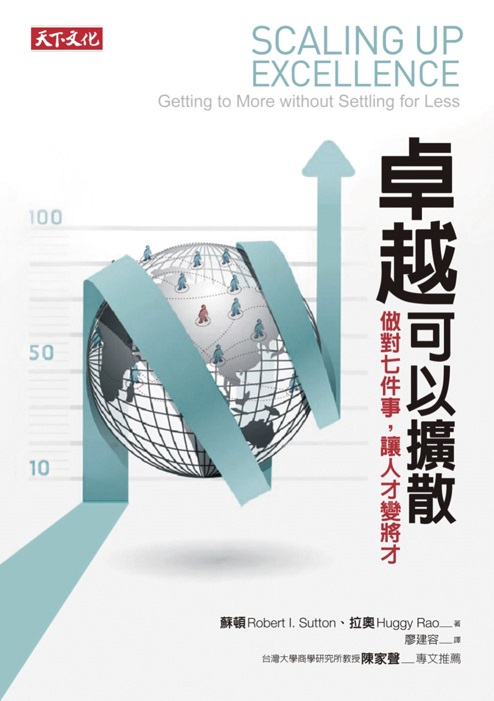網絡上流行了一句話,余華把歡樂留給了自己,悲劇留給了人物;1993年,余華以長篇小説《活着》在中國文壇上華麗亮相,他以冰冷的筆調娓娓述説着紈絝子弟福貴在家族沒落後,經歷着連串坎坷、悲劇和荒誕的命運,告訴我們生命承受之輕或重,都依然遵循自己的道路一直向前,警醒了我們關於“人是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思考。
時隔多年,這個愛講段子的男人,再次透過《文城》勾勒出小人物在大時代中縱橫交錯的命運。主人公林祥福與《活着》裏的褔貴一樣是大地主家少爺,然而林祥福為人殷實淳樸、重情重義,直到一天遇上小美,從此心裏有了歸屬,即便小美曾帶走家當不辭而別,他還是選擇原諒並迎來了女兒誕生,只是小美未曾許下不再離去的諾言,再次向南遠行。
為了尋找小美,為了讓襁褓中的女兒有個家,林祥福一路前往她口中的文城──那個一出門遇水,落腳得用船的地方。他四處打探卻一無所獲,最後來到了叫溪鎮的地方,遍佈文城的特徵,充滿小美的家鄉口音,也認識了林永良一家。至此,他帶着尋覓小美的希望在溪鎮安了家,清末民初年間,在軍閥和土匪混戰的亂世中,小美的影子從未消散,林祥福用盡一生尋找小美,卻不曾知道她曾近在呎尺,最後相遇已是墓碑和棺材之間。
讀余華的文字,恰如南方的冬,目睹一片枯葉跌入蒼茫,撲面而來的隱隱刺骨,翻湧的思緒足以耗上一整天。人們常說,冬天是荒涼的季節,正如林祥福在雨雹墜下的那個夜裏,感受着小美灼熱的體溫,也正如小美帶着透明破碎的清秀容顏在冰雪中離去……曾經的一往情深,曾經的愛恨交織,林祥福爾後越來越明白,他到不了文城,也離不開溪鎮,心裏一直有一個遠方,或是虛構的,或是前方未明的,代表着每個人的堅持和執念。
當回憶伴隨而來,也許曾經有那麼一個人,在生活中落下痕跡卻又轉身離去,讓你拼了命的把自己連根拔起,尋覓所蹤;走過了秋季,走進了冬季,某個夜色中他/她的身影忽然鮮明,忽然暗淡,你終將繼續前行走完自己的人生,在驀然回首間方才發現,他/她口中不存在的文城,卻是你用盡一生漂泊和找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