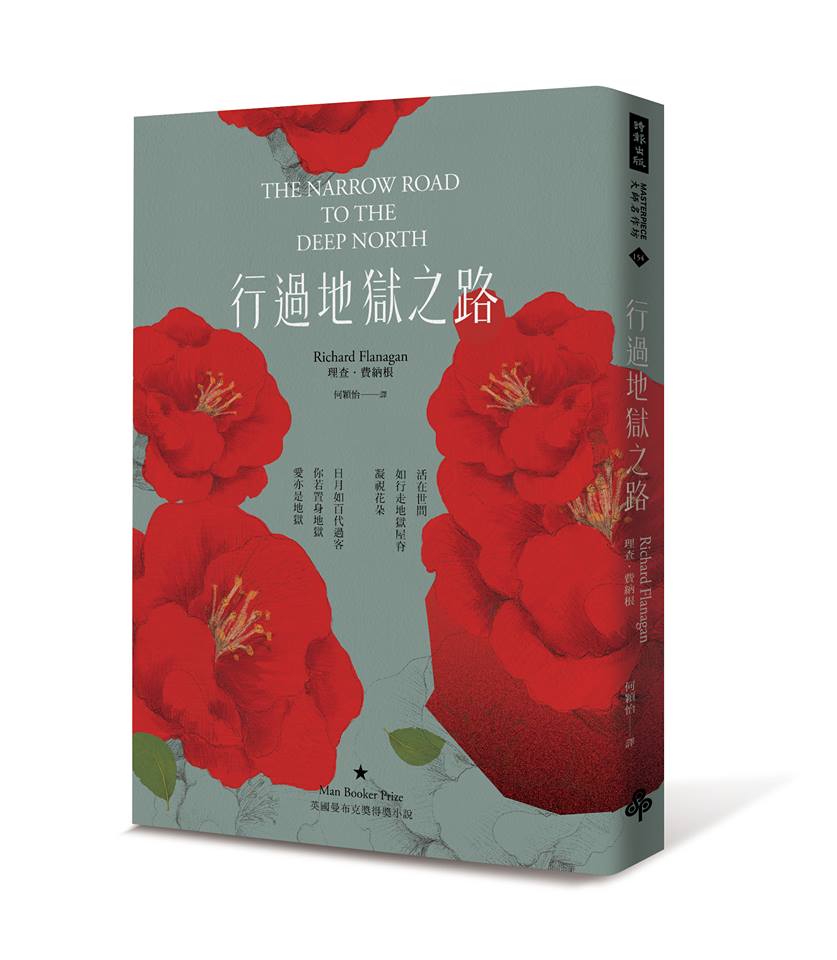導演塔倫天奴曾經在一個訪問提過,他拍電影的創作方向,是他在讀完一篇關於尚盧高達一齣電影的影評後,頓悟出來的。
那影評,是關於電影《法外之徒》的。影評人說,《法外之徒》就像是一個瘋了的法國影痴用美國偵探小說作骨架拍的電影,導演聚焦的,卻不是那小說故事,而是小說內行與行之間的詩意。懂電影的相信都聽過Film Noir這個詞語吧!Film Noir中譯為黑色電影,指風格晦暗、憤世嫉俗、視覺風格充滿抑壓、以低光源照明、善惡交織、帶夢幻感的黑白偵探片。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如果美國偵探小說沒有從傳統推理派過渡到冷硬派(Hard-Boiled)的話,相信,Film Noir這電影類型,根本就不會出現。傳統派偵探小說以解謎為主要方向,偵探與讀者身處於同一處境,閱讀時,讀者會有一種“有一個聰明能幹的偵探正跟我一起查案”的感覺,文筆具邏輯性,文學性不高。為了方便讀者可以知道謎團怎樣被解開,小說內總安排了一個沒甚麼缺點、精明能幹的偵探為讀者解剖真相。
冷硬派呢,則是反傳統、不大着重解謎推理部分的,故事中,偵探大多處於身不由己、被迫追尋真相的處境,他們不像傳統派小說的偵探般精明能幹、着重邏輯。反之,這些偵探大都有性格缺陷,沉迷酒精、毒品、女人、賭博的,都十分常見。
可是呢,就正正是因為這些冷硬派的偵探們在小說內無遮無掩的表白,以及小說中大量有關人性黑暗殘酷一面的描寫,令冷硬派的小說比傳統派偵探小說更具文學性。這些年來,以冷硬派風格寫成的電影、電視劇,不計其數。
村上春樹及保羅·奧斯特,是這20年來,最成功地把純文學推進主流領域的兩位作家。他們的成功,明眼人都應該看出,絕對歸功於他們那些匯合冷硬派小說的敘事方式,把本來文學味極重的主題層層推進的技巧。
在訪問中,村上及保羅·奧斯特都曾經提過,他們深受冷硬派重要作家雷蒙·錢德勒影響。讀過奧斯特小說的都應該看得出,他受另一位冷硬派重要作家達許·漢密特的影響可能更為深遠。以冷硬派的敘事方式把超現實、文學味極重的故事推進,就是這兩位作家的作品的重要特色。
如果說,村上及奧斯特的作品是以“偵探為骨架的存在主義文學小說”、“後設文學偵探小說”的話,以下介紹的這本《追想五斷章》可以說是一本“毫無文學意圖,但充滿文學意象的偵探小說”。
故事說的,是一名在舊書店工作、家道中落的大學失學生被一名女子委託,尋找他父親生前,分別在五本小眾文學雜誌刊登出來的短篇小說。女子期望,可以藉着這五篇小說,令她對去世的父親有更深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她渴望知道,父親在她四歲那年,究竟有沒有殺了她的母親。
這小說的作者米澤穗信,在日本被譽為是專寫“日常推理小說”的作家。日本推理小說類型分類極廣,所謂日常推理小說,即是以解決生活遇上的謎團為主題的推理小說。
說這本《追想五斷章》沒文學意圖,是因為閱讀時,你可以看到,作者只打算用最平白的語言、節奏、剪接把這個故事說完。字裏行間感受不到作者有一絲想把心胸內感受一下子傾瀉出來的文學衝動。
可是呢,由於故事本身就令人充滿文學想像,當中,男主角努力為女主角找回來,結局永遠留白的故事,也不得不令人想起波赫士那些令人沉思的迷宮小說。讀着讀着,令人不禁把這小說,跟村上與奧斯特的長篇小說比較起來。這小說的敘事方式平實,不會像讀村上與奧斯特的小說般,令人輕易進入高度感性、輕微恍惚的狀態,但閱讀時,會令人想到法國新小說派(Nouveau Roman)那些拒絕用感情色彩濃厚形容詞、反對隱喻、簡潔俐落的寫作風格。
把主流的東西加注詩意的作品,我們在塔倫天奴、法國新浪潮電影內、爵士樂中看過聽過很多了!把原本詩意的反轉,寫成一本主流的推理小說的則非常少見。不肯定村上與奧斯特的書迷會否喜歡這小說,肯定的是,若果你是那種喜愛看文學作家紀錄片,喜歡把作家的生平與文字對照的讀者,這一本小說,你一定會讀得津津有味。